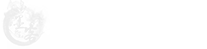扎根人民的最大收获(大家读书)
发布于:2019-09-08 09:24 阅读次数: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谈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总书记回忆起了一件往事,他说:“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人民作家柳青以其毕生的奋斗,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启示。为了纪念柳青的业绩,弘扬其精神,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柳青在皇甫》一书。我参与了此书的出版策划,读过多遍书稿。我感到,这本收录当年与柳青一起工作,与柳青有过接触,与《创业史》的创作、出版有关的众多人士回忆文章的纪念文集,以大量具体而生动的真实故事和真切感受,从不同角度描述了柳青作为一个人民作家的不同侧面和典型事迹,对我们走近柳青、了解柳青,有很多帮助与裨益。
扎根于人民之中
柳青在皇甫村安家落户的14年,人们通常看作是作家“深入生活”的典范。这样的看法没有错,但是只有这样的认识还不够。柳青从北京回到西安,从西安下到皇甫,都基于他的一个基本理念:“不要把文学当作个人的事业,不要断了和劳动人民的联系。”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深刻自醒与高度自觉,主导了他毅然决然地下到皇甫村,深深地扎根于人民之中,而且做到了完全和彻底。
《柳青在皇甫》中的不少文章,都谈到柳青有关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清醒认识。韦昕的《两个“尖端武器”》里谈到他1959年去皇甫村看望柳青时说到一些人对柳青的“自动下放”的不理解,柳青以肯定的语气回答:“作为一个作家,深入生活,研究生活,仍是第一位的工作。”针对一些人要多走多看的说法,柳青又回应说:“到处去看看,我不反对,但最好是在生活中扎下根去,深入生活,解剖麻雀,一个生产大队就是一个社会嘛。”郭盼生的《夜寻王家斌》里说到他去看望病中的柳青,谈及在皇甫的14年,柳青坚定地说:“我还是一句老话:要真正体验生活,必须深入生活;要塑造英雄人物,必先塑造自己。”柳青在不同时期所给出的这些说法,道出来的都是颠扑不破的文学真谛与人生真理。这种清醒的认识、坚定的信念,构成了他落户皇甫、扎根人民的根本动因。
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记述了柳青在皇甫落户后的外在样态和工作状态。邓攀、冯鹏程的《县委门卫挡错人》这样描述柳青在乡下的样子:“身穿对襟布衫,脚蹬布鞋,老戴一顶西瓜皮帽,外出有事,常骑着他那掉了漆皮的自行车。”郭盼生的文章写到,因为柳青“从发动农民卖余粮,到组织互助组,建立合作社,他熟悉了皇甫村的每一户人,皇甫村发生的大小事情,他都要弄明白,都要帮助解决好”,村里的干部感慨地说:“这里的合作化运动,柳书记是圈囤身子钻在里边,泡在里边的。”一个“钻”,一个“泡”,生动又形象地勾勒出柳青工作投入的深切与忘我,这样的一个状态,才配得上叫“扎根”。
徐民和、谢式丘的《在人民中生根》一文,有很多有关柳青在皇甫的描述:“在皇甫村,柳青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他和村里的共产党员在一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和普通农民一起参加合作化运动,每逢集日,柳青也挎着篮子,放上几个油瓶,和农民们边走边谈。农村的婚丧嫁娶,架屋上梁,他也跟上群众,挤在人堆里,甚至大人小孩吵架,他也凑上去看着、听着……”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柳青“与皇甫村的庄稼人结成了亲密无间的鱼水关系。他能叫出村里几百个人的姓名,熟悉成百个家庭的历史和几辈人的性格。皇甫村的庄稼人也了解他。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黑瘦的老汉,也是个庄稼人。”这里实际上也说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柳青已经把自己“农民化”,也等于实现了“去作家化”。他在改造旧有的自己,重塑全新的自己。这也是柳青落户皇甫村的本意所在,扎根人民的最大收获。
与人民一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