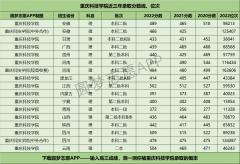口述人:蔡江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兼职教授)
采访:柴宗盛(澎湃新闻记者)
时间:2018年9月8日
地点: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蔡江南近照父母影响我老家山东禹城,父亲出身地主家庭,是家中独子,爷爷早早过世。抗战开始时,父亲读中学。学校要随政府南迁,刚强的奶奶,狠下心来让独子随学校一起南迁,从山东一路转移到了四川。
在大时代,人的命运说不清楚,父亲的学校当时有很多进步学生和地下党,有一批学生去了延安,因为有文化,很多人成长为高级干部。本来父亲也准备去,但在去之前决定回家看母亲。他们几个同学一起回山东,在路上被国民党三青团稀里糊涂地吸收了。后来因为这段经历,父亲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回一趟家的功夫,命运完全改写。
父亲到了山东,在他大伯支持下,到济南读了一个师范学校。山东解放后,他随部队南下到了上海,参与接管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父亲负责资料室工作,相当于电台的图书馆。
父亲是一个科级干部,他的工资有一百多元,在当时算高薪了。我母亲在宋庆龄创立的中国福利会托儿所工作,自托儿所创立她就在那里工作,后来做到相当于教导主任的职务。
我家可以算是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习惯,每天记日记,大概从1940年代开始,一直记到2007年去世为止。几十年的日记都保留着,从那里能看到国家的历史,也可以看到个人和家庭的历史。
我家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有妹妹和弟弟。父亲每个周末都会把图书馆里的杂志和书带给我们,都是偏文史方面的读物。那时候我们很盼望周末,从小接触了不少文学作品,还有电影戏剧等文艺作品。
父亲一直做媒体,我对媒体天然有亲近感。我们家的房门后有块板,我经常在上面写写画画,父亲为此感到骄傲。我在小学、中学都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大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以学校对我的锻炼就是出墙报。那时候我们要像记者一样采访,写稿,在板报上写美术字,画画,由此锻炼了我的写作编辑能力。

蔡江南中学时代。上山下乡“文革”开始后父亲被下放到南京,上海在南京有个梅山铁矿,又称9424厂,他在铁路上当拌道工。我中学毕业时父亲还在南京,那时中学毕业分配工作,因为父亲不在上海,我作为长子可以留在上海,去企业工作或者技校念书。但我还是选择了下乡,我妹妹比我小一岁,如果我下乡,她就可以留在上海。那时候,我们非常追求“进步”,我特地要选择去所有目的地中最艰苦的安徽农村。因为自己是团支部书记,觉得应该发挥带头作用,这是人生路上第一次重要选择。
到那才知道被分配到了安徽黄山茶林厂的制药厂。刚去几个月后,一个六月天的中午,厂里两吨大的开水木桶底脱落了,滚烫的开水喷涌而出,直接泼到我身上,腿和脚被严重烫伤,烫伤面积达到人体17%。我自己走进医务室,水桶距离医务室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路上留下两行血印。那时是夏天,烫伤非常容易感染,一旦感染就有生命危险,我们一起下乡的同学忍不住流泪,因为说不定会发生什么。
烫伤要做清创手术,当时被送往上海在安徽的三线医院,用了针灸麻醉,还是挺管用的。在那儿住院一个多月,情况逐渐稳定,然后送我回到上海养伤。由于我的疤痕体质,伤口脚面长了一层像乌龟壳那么厚的息肉,把脚趾也连起来了,没法走路。母亲找到一位仁济医院整形外科的家长,帮我做了整形手术,把这层壳去掉,从大腿上取了两大块皮,移植到脚面上。因此,我在床上躺了大约一年时间。
我利用这个时间学外语,对后来高考和读大学都帮助不少。

1976年总理去世时蔡江南在上海家里养伤时画的周总理画像。我的大学伤好以后,继续到黄山下乡。
1977年要恢复高考了,在安徽农村,我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也不了解大学的情况。我父亲在南京看到新闻,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还给我买了辅导的教材。我对学习一直保持着热情,在农场里自己坚持自学英语,当时只是出于爱好,并没有明确的目的。
那年农场里大约有几百人参加考试,第一批只录取了七个人,我是其中之一,也是当时录取的唯一文科专业学生。然而我的其他三个志愿(1.复旦新闻系,2.华师大外语系,3.复旦中文系)都没有被录取,最后被录取到华师大的政教系。四人帮被粉碎后,大家对政治都不感兴趣,我志愿里没有选这个专业。那年上海高考招生办主任是华师大校长刘佛年,事后传说,那年华师大拥有招生优先权。
政教系分三个专业,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在第三年时分专业,我选了经济专业。那时候在选专业上没有什么成熟想法,由于在大学前两年中认真读了《资本论》原著,对经济学比较感兴趣,就选了经济学专业,事后证明这正好是社会非常需要的。
在决定参加高考和大学选择经济学专业上,自己当时年轻,做选择时还处于比较朦胧的状态,但这些选择恰巧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和需要,也给个人成长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我追求上进,但不算天生就有极强奋斗精神的人。本科毕业后我考了复旦的研究生。本来那时的本科生非常稀缺,有很多很好的工作机会,也有很多从政机会,不过当时从政并不像后来那么热门。由于工作机会很多,大家对继续读书并不很感兴趣。
虽然好工作很多,但毕业生去哪儿还是要分配的,自己没有选择权。上海的学生有一部要被分配去外地,年纪大的、已经成家的会留在上海,年纪小的很可能去外地。要想留在上海,考研究生是比较保险的选择。
我选择备考复旦经济系的研究生。复旦那时候学得比我们深,我心里没底,当复习遇到挫折时一度想放弃,但家人都鼓励我。其实我挺希望他们同情我,说太苦了,别考了,那样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了。
考完之后,复旦经济系现代西方经济学这个专业我总分考了第一。这说明我比较不自信,容易低估自己。这也许与家庭教育有关,我母亲的教育方式比较传统,这也是中西方教育最大的区别。自信是成功非常重要的条件,中式教育的严格,很容易把孩子的自信心打掉。老师批评,家长批评,都是指出缺点,不表扬优点。西式教育注意培养自信,西方人在哪儿都是信心满满,往往高估自己,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有勇气推销自己。
本科和硕士的七年学习,为我在经济学理论方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我自己读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经典原著,一边读一边翻译,之后还参加翻译了三本西方经济学著作。研究生的经历对我在学术生涯道路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证明考研是一个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