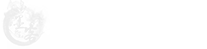《北京文學》執行主編:文學雜志首先是為讀者辦的
发布于:2019-10-03 18:57 阅读次数:
原標題:文學雜志首先是為讀者辦的(慶祝新中國成立70年·文學期刊篇⑤)



楊曉升
關注現實生活和尊重讀者
何 平:你是先做《北京文學》的作者,然后2000年從《中國青年》調到《北京文學》做執行主編的。世紀之交,正是文學期刊的生存很艱難的時刻。你為什麼偏偏在那時候作出這種選擇?
楊曉升:作出此種選擇,是多年的文學情結使然。再則是那時候全國的文學雜志大都處於低潮,低潮的原因之一是媒體的蓬勃發展和文化的多元,讓讀者在文化消費方面有了多種選擇,文學雜志再不可能像傷痕文學初期那樣一花獨放、洛陽紙貴,由此帶來的文學雜志讀者分流、發行量日益萎縮的局面,是自然而然的事。面對文化環境已然發生的變化與轉型,文學期刊自身普遍仍缺乏應有的自我覺醒和自我反思,存在閉門辦刊、孤芳自賞的現象。而我認為,文學雜志既然是公開發行的刊物,首先是為讀者辦的,應該將讀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壞和刊物的好壞,首先必須交由讀者檢驗,作家的創作和刊物的出版,都應當力圖為大多數讀者所喜聞樂見,惟有如此,文學雜志才會有生命力。我選擇到文學期刊工作,正是出於此種判斷和考量。
何 平:《北京文學》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但我覺得和今天《北京文學》關聯性更大的重要起點是《北京文藝》更名《北京文學》的1980年前后。現在文學史上經常提到的這一時期《北京文學》(《北京文藝》)的經典作品很多,像《在靜靜的病房裡》《話說陶然亭》《內奸》《愛,是不能忘記的》《風箏飄帶》《丹鳳眼》《受戒》等等。一下子集中出了這麼多好作品,顯然和大量的文學期刊沒有復刊和創刊有關系,《北京文學》佔了時代的先機,也順勢成就了刊物關注時代、介入現實的傳統。主編的趣味肯定會影響到刊物的趣味,你的資深記者和報告文學作家的從業經歷,正好和《北京文學》的精神傳統暗合。
楊曉升:新時期文學始於“文革”結束和改革開放初,那時候全國各地的文學期刊已經如雨后春筍般復刊或創刊,《北京文學》之所以能在那個時候發表了大量優秀作品,一是因為刊物對首任主編老舍、趙樹理文學理念的傳承——對現實生活的關注和對讀者的尊重,半個多世紀以來,刊物一直提倡發表雅俗共賞、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作品,同時那個時期編輯部先后聚集了李清泉、林斤瀾、周雁如等一批優秀編輯前輩,而北京首都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使《北京文學》在新時期文學得天獨厚,佔了先機。直至我到《北京文學》任職之前的一段時間,《北京文學》其實也已經感知外部社會生活和文化環境的變化,在文學關注現實、以期贏得讀者關注方面,也已經進行著新探索,90年代末期影響巨大的“憂思語文教育”問題討論,正是在這個時期產生的。
發現和推薦文學新人是責任
何 平:《北京文學》在林斤瀾1986年擔任主編后曾經有一個先鋒文學的階段,這一階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地推出了余華,當然從《北京文學》一貫注重發現和推薦文學新人的傳統上,可以得到一種解釋,主編、編輯的趣味和時代文學風尚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楊曉升:確實,刊物的風格說到底主要是主編的風格。林斤瀾任主編的那個時期,新時期文學正經歷嬗變,作家的創作方式正由過去的單一轉向多元,先鋒文學也正是那一時期的產物。總體上講,《北京文學》自創刊以來,一直是以傳統現實主義的風格為主的,林斤瀾任主編時,文學的多元發展以及他個人的趣味,使得刊物出現對先鋒文學的關注與探索,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發現新人、扶持新人一直是《北京文學》的責任與傳統。再者,對新人的發現,才華和潛力是編輯部考量的主要因素,所以相對更加寬容,即便他提供的單篇作品與刊物的總體風格上不很吻合,隻要是他作品顯露出獨特的亮光與特質,編輯部也都會區別對待、唯才是舉的。
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最重要
何 平:你是從2001年開始對《北京文學》進行改版的。在此之前,《北京文學》曾經有幾次大的欄目調整。1996年,增設了“世紀觀察”和“百家錚言”﹔1998年,又增設“思想者訪談”﹔1999年和2000年增設的欄目更多更雜。這些努力試圖矯正和改變傳統文學刊物的按文體幾大塊的僵化的欄目組元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話題性的當下性和公共性、對話性很強的“世紀觀察”和“百家錚言”欄目,鑿通了文學界、知識界和大眾讀者之間的壁壘。你對《北京文學》這幾年的欄目調整怎麼看?你的改版從這些調整中得到啟發了嗎?
相关教程